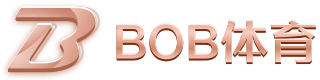B体育王凯军老师的《环保回忆录》2022年11月正式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后,受到业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,深深触动了一代环保人的心。
阅读本书,如同一览王老师丰富的人生风景,更可感受到他对环保事业的深沉热爱,对师友的深笃情义,对人生与事业关系的深刻认知。
整本书王凯军老师谈论的都是40年职业生涯中难忘的师长、友人的故事,以及他在行业当中创造与发现的故事,他借着时间与专业领域相结合的整体架构,来发展他的观点,陈述他对环保与人生主题的理解。
这本书和历史有关,但毕竟是科学技术专家写的,所以不是编年史,因为科学家跟历史学家相反,他们要摆脱时间与地点的限制。在这本书中,王老师想要说的是一般现象,事物变化的一般规则。
因为是和环保相关的书,书里确实也有一些专有名词,如果有环保行业的背景知识,阅读起来会更顺滑,但对这些词不懂也没关系,一样能看明白书所表达的意思。
王老师讲述过程中的部分精彩内容,在最终的成书中略删减掉一些文字,为了弥补这个小小的遗憾,我把其中一些原汁原味的内容摘要出来,以飨各位读者。
江小珂当过两年北京环保所的所长,后任北京环保局的局长。江小珂不只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环保局局长,从中国环保史的角度,她是建立起了中国环保的基本体系。
在北京环保界,提到江小珂,几乎无人不晓。她生于1929年,自70年代初从事环保事业以来,她的名字就与环保联系在了一起。除了环保所的任职经历,她还曾任北京市环保局局长,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、北京环境保护基金会会长。1972年还作为中国代表团惟一的女性成员,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。
江小珂为人非常正直,她本身是老北京市委,她的丈夫是当时北京市市委的纪委主任王军。
第一件事是胡YB当的时候,引进日本投资,批准在密云建一个游乐场——当年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,因为咱们国家没有游乐场,所以要建一个。都建了一半了,江小珂坚决反对,说水源地世界各国都是保护的,不能做这种旅游开发。她非常强硬地把这件事制止了,跟直接叫板,密云水库得以保护下来。
第二件事就是首钢搬迁。汪GT说首钢有污染,最后在市长开会的时候,江小珂就把大气污染的数据拿出来,说多少污染是来源于首钢的,坚持提出首钢必须要搬迁。最后市长也顶不住压力。大气污染治理后期,江小珂已经不是北京市环保局局长了,是中国环保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长。
我国初期所有新出现的环保政策,很多都是起始于北京市,是江小珂发起的。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,环保政策开始涌现,我国完成了三同时制度,环评制度、八大制度,后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认,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把环境政策捋出一条线,而且这条线应该说是很合理的,说明下了很大功夫。
对比一下曲格平,一位普通退休的部级干部,而且在任的时候只是副部级干部,这在中国多了去了,为什么现在有这么老的资格?就是因为他们做的是为整个环保行业政策管理体系立梁架柱的事,是奠基者。
当年这些重要工作,很多都是首先在北京市做,当时正是江小珂任北京市环保局局长,所以实际上是曲和江他们共同推动了中国环保行业的管理体制构建。
汪在北京的时候就又搞了一个京津冀水资源项目,在那以前的项目是李宪法带着王ST搞的,又有这个新项目时,时任北京市环保局局长史捍民就找来王ST,让他负责。
汪GT当时还想评选院士,当了部长他还参评过一次,就是因为这些部长们也来参加院士评选,后来才出了管理人员不能参评之类的规定。
但是确实汪GT在水资源领域研究做得比较深,在北京也是没日没夜钻研,晚上想起来什么就给局长打电话,当时因为这个水资源课题整天跟北京市市长开会,结题以后去申报国家奖。
王ST因为是负责人之一,就由他代表去做报告,在评选环节,他讲了一半就说:“没什么意思。”就不讲了,最终就没评上奖。搞完了以后,汪GT大为光火。可见王ST也是很有个性的人物。
在李宪法时期,环保所基本只做国家课题项目,到聂桂生开始有了承包,并建立了一系列的承包制度。每人完成定额,再进行奖励提成。每个人每个课题分别一本台账,各种支出报销都给记在这本子。这本子好比一个银行卡,什么都能报销,没有限制。
承包制度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,大家在市场上非常活跃。我们相当于跟公司竞争项目,不仅可以搞设计,也能搞工程。那时候也不需要工程资质,签一个200万的治理项目,找施工队再供设备就完了。B体育所以,环保所在这一期间发展比较快。
一是环科院的通病,大量的人出去搞环评。对于环科院的人来说,搞了环评就和吃了一样,因为挣钱太容易了。那时候正赶上我国大规模上建设,建个楼房都得做环评。环保所40%左右的收入来自环评,没成本,提升快,又是自己的小金库。地方的环科院,环评占的比例更高,有的超过50%。这样,工程占比自然就少了。那个年代,只要做过环评,再搞深入的研究就比较难了。
二是承包机制造成了环科院领先的技术虽然很多,却并没有一个技术走向产业。他们都搞得非常早,但很少留下来。这些人基本上小富即安,让他去创业,他绝不会去,让他离开环科院到企业去,他也不会离开,为什么?当时创业不一定有在环科院拿到的课题费用多。接三五个环评项目就是二三十万,搞得好一年挣五六十万甚至七八十万都不是问题。这在90年代中期,都可以在北京买套房子了。这种管理上班随便,想不去就不去没人管,一年不见面,一月不见面,工资照发。
郑元景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,包括Lettinga的影响也是一样的,我们现在在很多事情上的看法是一致的,比如对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的看法,比如对下水道的看法,他也主张源分离的下水道,还有对创新路径的看法。B体育
那是因为他所有的论文我全读过,虽然他跟你接触时直接说得很少,但是对你的影响还是深远的。
为什么人家国外花钱资助你到美国去,资助你到英国去学习,因为你回来以后就是打着美国、英国的烙印。你去了以后,哪怕不会刻意地去说、去想,你在生活中,在聊天的过程中,也会提到国外怎么样怎么样,去了以后欧洲怎么样怎么样,就是会打上这样的烙印。
过去的厌氧,大家都是用钢筋混凝土,钢混的形式,所以过去的环保产业很大部分是土建项目,实际上技术在里面占的比例非常低。
利浦罐主要是用来储存粮食的。它的特点是制作周期特别快,标准化程度特别高。所以王老师提出来:是不是可以用利普罐代替钢筋混凝土结构,把很多过去给建筑业的一些产值变成真正变成环保业的产值。当时我听完以后,感觉这个想法非常好。所以就在山东的项目上率先推出了一个利浦罐。
当时很多工业企业的达标期限,B体育政府要求得很紧,如果用钢筋混凝土,周期非常长,冬季还没法施工。用利浦罐之后,过去要一年工期的项目,现在三个月就基本上完工了。所以,利浦罐在市场上用户接受度非常高。
从环保企业来讲,过去做一个项目可能拿到的产值只有30%,现在一下子变成了70%,B体育等于过去要做两个项目,而现在做一个项目就把产值完成了。这就是一个双赢效果。
利浦罐后来也成为十方主打的环保装备,大家都感觉这个技术特别好,所以目前整个环保产业,厌氧都以利浦罐为基础。
后来又有很多变种,包括拼装罐。这种理念,是装备化、标准化,现在在环保产业已经形成主流。
应该说,王老师提出的利浦罐,厌氧标准化、产业化的这种理念,对整个环保产业的影响很大。
标准化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很多事情你要想复制,没有标准化的东西是很难的。如果一个项目一个样,管理,各方面的难度,误差性,都会非常大。
所以从一开始,我们就把主要工艺都固化在一种标准化的产品上。应用中,只要是同一类的项目,只是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,选择不一样的套数就可以了。我们的技术都是产品化、标准化的,对员工培训容易做,现场就是组装拼装,工期也快。
我虽然是搞研究的,却也算是草根出身。去过各种工厂,自己做设备,还搞过包工队。这些对于我来说,并不觉得苦,反而乐在其中。或者可以说,这正是我热爱环保行业的根本原因。在这些新鲜的边界里,我追求新的知识,参与新的创造,不断给我带来快乐、满足与升华。
最早是在环科院的时候,管理非常自由,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和机会去做外面的各种项目。从这里开始,我的“朋友圈”开始往学术科研之外的人群扩展,链接了一群形状各异、有声有色的人,其中的很多人成为了我的好朋友。我喜欢他们,如同喜欢这倏忽百变、纷繁热闹的环保行业。
印象中第一个外部的甲方是可口可乐公司。当时我还在高碑店做中试,北京可口可乐要建污水处理厂,采用了供货商的设计,请我去看看这个方案。我对那个设计不太认同,就写了个意见书,说花钱太多,太不合算。
可口可乐公司觉得我说的很在道,就请我们去做设计。设计结束后,正好徐东利的哥哥做土建业务,他便加入了进来,帮着做建设。就这样,我们从提意见开始,变成了总承包,从头参与到尾。我在这里头改来改去、跑来跑去,折腾一圈后,对工程里的这些道道就烂熟于心了。
后来和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五里店项目的合作也非常有意思。我们先去参观刚引进的生产线,看全自动的现代生产工序将进口原浆变成可乐,这给80年代的我们带来扑面而来的震撼。
比这更有意思的是在项目中结识的一个哥们。他是个,刚退伍时在五里店的可口可乐厂保卫科当科长,连办公室都没有,如果来了重要客人,他就拿张报纸去蹲厕所,躲起来。这样的窘境一点没让他变得灰心,他充满热情,什么都学得快,后来开始管基建,所以和我们有合作。合作完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,过年都要聚一聚,后来买房子也买在了一个小区。
这哥们后来当了亦庄那边可口可乐公司的副总,快退休时候又被派到天津公司当总经理。去的时候,天津可口可乐是亏损的,两年以后,天津公司成了中国区销售量的第一名,再后来成了全球最盈利的销售团队,连续三五年是销售冠军。为此,他延期退休了好几年,可口可乐全球的总裁好几年邀请他到家里做客。身份转变后,他的性子还是一如既往,过年时,见到扫厕所的大妈都非常亲切地握手,和大妈说“沾沾您的喜气”,吓得大妈直往后躲。
除了做外部项目,我在做环评的过程中也接触到了很多不同领域。一开始我也没有做过环评,因为和环保局的一人相熟,在北京引进第一套精制油生产线时,他找到我帮忙做环评,我便从善如流地去了。
在和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,我亲眼看到机器先把黄豆压成0.2毫米厚的豆粕,用汽油把压出来的油脂成分浸泡出来,再把汽油给蒸发掉,这才产出了毛油。这套流程鲜活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,成为了我感受外部世界的一个精巧单元。
当时和我们打交道是北京粮油公司的老总,很有特点,不拘小节。B体育因为所处行业的关系,他一直喜欢讲那个卖油翁熟能生巧的故事。由于这次环评,我与他熟悉了起来,后来在政协与他也经常见面。
还有啤酒行业,让我知道了80年代的啤酒酿造中,酵母发酵后的液体需要用硅藻土过滤,过滤后罐体需要反冲洗;后来为了推沼气厌氧,我跟老甘到了浮来春酒厂和厂长打交道,大家一起醉倒后,也成了好朋友,后来还一块去日本。
每做一次项目,接触一个新行业,都会认识一些朋友,学习一些新知识。从环保的角度切入,使得我接触到的各行人员大多是行业精英,与他们打交道,很快能够了解行业的技术精髓、产业结构、发展状况等,受益良多。